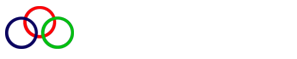高二文2班 邓雅匀
指导教师 陈冬艳
第一次搬家我正好三岁。从东边小岛上来的东瀛人提着枪踹开了叔叔家的院门,父亲闻讯携着一家老小还有数十人仆从往南方逃去。那时我还小,只是朦朦胧胧地记得家里一团糟,父亲把台架上能砸的都砸,念念叨叨地说不能给小鬼子摸走了之类的。我年小,做不了什么,让哥哥牵着手杵在一边,还含着大娘给的麦糖,不过现在已经忘了味儿。
第二次是在北平的四合院里,刘老先生正逼着我背《短歌行》。在我第九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时候,大管家匆匆地推开门,跟老先生语速飞快地说了些什么后,一把抄起我吼了声:“小少爷抓紧我的衣襟子!”便跑得跟疯掉的来福似的。当时他是扛着我跑的,所以后来坐在马车上再一次南下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胃被绞成了梭子,一阵地干呕。那次搬家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胃痉挛。
继南下之后,我们在浙江安了家。若大的江南庭院恍恍惚惚绕过我十年的岁月,屋顶上长了几根绿芽,檐下的燕子换了一窝又一窝。东瀛人再次提枪南下时踹了全城的门唯独踹我家大门时轻了些,他们掳走了照顾我起居生活的青丫头——她再也没回来。家里隔三差五地会来几个用倭语的矮个男人,他们总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着我的母亲,或者教我一些像三岁幼童画的画般的字并让我发出一些莫名奇妙的音节。每当他们离开父亲就会不断的叹息,然后用一种悲伤的目光看我。我或多或少明白什么,但又说不清是些什么,只是默默地服从。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上了曹孟德的《短歌行》。这首充满了那个阴谋家的野心的诗在那群倭人教我那些所谓的倭语之后我都会背一遍,然后望着天,想那幼时教我识字的
最后一次搬家在我十九岁,东瀛人跑了,父亲被迫必须离开。那天街坊全聚在我家院门口,用冷冰冰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年过半百的管家偷偷告诉我:“哥儿,他们以为咱们是汉奸。”我没说话,降母亲扶上车后自己也坐了进去。过了好多年,我终于发现所谓的搬家竟是诀别!诀别了那生我养我的故土!我后悔,后悔在登上甲板的那一刻没有醒悟,后悔在有意归乡的那一刻没有勇气买张船票... ...
然而,我老了。糟糕的身体状况拒绝了我再次踏上故土愿望,使我只能躺在落地窗前的病床上,望着大洋彼端,听儿孙用蹩脚的国语背诵: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从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儿的麦糖没有故乡的味儿啊... ...我默默闭上了眼。